一张奖状,我的起点
周舒
2023年的初夏,我从北京返回江宁湖熟的老宅定居。在收拾屋子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张奖状,时空的大门瞬间打开,叫我重回少年时代。
2005年,十八岁的我从江宁高级中学毕业,离开家乡,远赴首都求学,自此淹留十八载。广阔的天地给予了我极大的自由空间,最终找到了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从一个码字人慢慢成为写作者,如今忝为一名作家。
然而,回首这写字卖文以谋稻粱的前半生,发现自己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在书写别人的世界。而这一张奖状,让我找回了自己文学生涯的起点,我意识到,返乡定居、闭门静书、安心写作,才是我命中注定的选择。
这张奖状是刚上高中的那个秋天获得的,也是我在母校拿到的第一张奖状。回想起来,刚上高一的那会儿,我还是挺受打击的。初中时代所拥有的种种名列前茅的光环消失了,曾经自以为是学霸的我,发现考入咱们学校的个个都是大神。而且,随着学习的推进,我的理科短板很快暴露了出来,所以整体成绩并不是很优秀。唯一幸运的,我还有一个写作文的长处。
这篇参加南京市中学生文学总社第七届金秋笔会征文的作文究竟写的是什么,我已经浑不记得了。但题目《银汉无声转玉盘》出自一代文豪苏东坡的《阳关曲·中秋月》词:“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想来,我的文章主题应该是种种离情别绪吧。可正如辛稼轩所言:“少年不知愁滋味。”纵然那时的我文章写得不错,恐怕也不能真的明白什么是人生百味。
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学期我从校图书馆借了一本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每天晚自习做完作业后就乐滋滋地拿出来看。一天,值班的班主任发现了,她走过来翻看了书的封面,又默默走开了。隔天是英语老师值班,她也发现了,但没有保持沉默,而是十分忧心地和我说,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书上。
这些年里,每每和朋友们谈论起中国应试教育的话题,我都会说起这个故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为我鸣不平,说班主任很开明,英语老师就太死板。她要是知道,你后来就是因为喜欢《红楼梦》而坚定了文学的道路,成为一名作家,当时还会这么说吗?这时候,我会非常认真严肃地告诉对方:“可是,如果没有高中那段披星戴月、背书刷题的日子,我可能都考不上大学,不可能来到北京读书、工作,更不会拥有如今的一切。”
前两年,一个“小镇做题家”的话题在网络上激起了千层浪,把我们这些从城镇走出去的莘莘学子都打上了一个标签。很多人觉得这是贬义词,我却认为,“小镇做题家”反而是我们最好的人生注解:这世上,任何一个为了追求理想而不顾一切去拼搏、去努力、去创造美好未来的人,都是值得赞美的。
入学的时候,学校还在宁中巷,一条长长的水泥道连着校门,门后面,是被两侧荫荫梧桐掩映着的教学楼。升入高三的那一年,学校搬到了天元东路,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母校的70周年校庆。当天的午饭是免费的,每个人的饭盒里都有一大块猪排,我吃得不亦乐乎;晚上的文艺演出也是我们那一届高三岁月的最后狂欢日,若没记错,女主持人是当年刚刚获得了“新金陵十二钗”南京形象大使选拔第一名的校友刘婧。
如今,二十年光阴倏忽而过,母校又迎来了90周年的生日庆典,真叫人感慨万千。校园里面的小师弟、小师妹们还在努力刷题吗?纵然如此,他们的视野也肯定比二十年前的我更加开阔,人生目标也更加多姿多彩。
在江宁高级中学读书的时候,最喜欢穿着校服出门,尤其喜欢在放假的时候穿着校服回家,因为母校的光环总会为我赢得一些赞许、欣赏的目光。那时候也曾悄悄想过,自己将来有没有可能做出一点点成就,为母校挣得一丝丝的光荣的呢?
如今,我固然有了一份答卷,但扪心自问,这答卷似乎还是单薄了些。但是没关系,我不妨遵从母校的校训——崇德力行,在漫漫的文学之路上继续向前奔着,用更多更好的答卷,为她以后的每一个生辰献礼。
*** 校友简介:周舒,笔名周如风、舒燏。2005年毕业于江宁高级中学,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曹雪芹学会会员、《中华遗产》《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作者、“书香中国”读书活动主讲人。
已出版《情到此间怎由人》《暮春花尽留与谁怜:宫体诗中的情与怨》《纳兰诗词赏读》《几回清梦到花前:红楼女子的草木情缘》《雪里春信李清照》《仗剑千年辛弃疾》等个人文学作品9部。其中,《几回清梦到花前:红楼女子的草木情缘》一书入选中国外文局2020年度优秀外宣作品“十大中国好书”。2023年,凭借《雪里春信李清照》一书荣登第九届当当影响力作家榜。
在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举办的“书香中国”读书活动中担任主讲人,举行线上、线下文学讲座十余场。与中央电视台《中国影像方志》《花季中国》《地理中国》等栏目以及中央新影集团的纪录片小组合作,参与策划、调研、撰稿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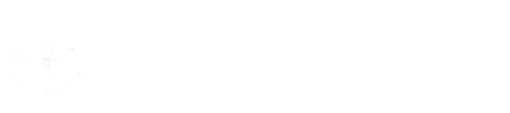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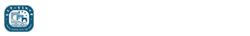



 共研•共进 :基于课例的教研有效性
共研•共进 :基于课例的教研有效性
 共研•共进 :基于课例的教研有效性探索
共研•共进 :基于课例的教研有效性探索
 苏公网安备32011502010134号
苏公网安备32011502010134号